
4G商机
吴磊/文
2003年12月4日,中国4G牌照发放,三大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各获一张TD-LTE牌照,由此拉开中国4G正式商用的大幕,整个通信产业迎来3G之后的新一轮投资盛宴。如果把3G比作4车道高速公路,那么4G就是32车道高速公路。数据流量的井喷也许会带来电信商业模式的加速变革,而更重要的是,流量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宝贵的基础资源,对整个商业世界足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以3G向4G的迁移为技术背景,基础电信业务向民营资本敞开大门,虚拟运营商入场,则是这一轮产业变革的新特征。新鲜面孔,各色玩家,三教九流,登台亮相。这是一群“门外汉”,也是“野蛮人”,他们或许姿势不完美,或许赤裸裸,但沉寂太久的电信市场亟需几条“鲶鱼”唤醒肌体的活力。而那些沉睡不醒的、有心无力的保守派,则注定要跌下神坛,从中心滑向边缘,躲进历史的暗处。
虽然4G已经发牌,但眼下并非真正的4G时代,套用一个流行句式可称之为“3G之上,4G未满”的后3G时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预计4G可能带来的种种改观。相反,因为有了3G长达5年的铺垫,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推测接下来的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还会产生哪些奇迹、颠覆以及反转。
一组来自 爱立信 的基础数据首当其冲值得重视:
到2019年,全球手机用户将接近93亿,其中56亿为智能手机用户、26亿为LTE用户;
到2019年,WCDMA/HSPA网络将覆盖全世界90%的人口,LTE网络覆盖率65%;
2013年至2019年,智能手机用户将增长两倍,智能手机数据流量将增加10倍;2013年视频流量占移动数据总流量的35%左右,这一数字在2019年将达到50%以上;
未来几年,中国将从2G/3G网络迅速转向4G网络,到2019年底,中国LTE用户数将超过7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4G LTE市场。
可以肯定的是,4G会大体遵循3G的发展轨迹——网络基础设施先行,带动新型终端出货上量继而低价普及,匹配底层技术的上层应用从消费端开始涌现,进而深入企业和组织内部,量变积累出质变,潜移默化地变革社会生活。
技术与商业结合形成的张力,越来越显性地、甚至有些夸张地推着地球旋转。史学家、预言家们大胆断言:人类自农耕文明、蒸汽文明之后迈入了数字文明,而权力的表征则从水流、石油变成了比特。
终端的狂欢
如诸多ICT报告所预测的那样,全球网络——不论是互联网还是企业网——的数据流量正呈现几何级数增长。来自 思科 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移动数据流量将达到每月10.8EB。
搜集这些海量而又千奇百怪数据的“罪魁祸首”当然是终端。不过今天再谈论终端这个词的时候,其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汽车、手表、眼镜、鞋、首饰、家具等等一切用得到用不到的东西,都是数据的秘密采集者。
一年一度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简称CES)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移动通信展(简称MWC)堪称电子产品和最新ICT技术的风向标。而2014年的CES和MWC毫无悬念地被各种冠以4G名头的终端抢了头彩。
在 高通 公司眼里,CES展览“联网汽车、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家居和可穿戴设备等济济一堂的趋势必延续多年”,高通自己展示了采用4G LTE技术的奥迪A3联网汽车和一款能够实现整个家庭范围内音频串流和智能终端间互操作的智能手表。
除了高通展出了汽车外,还有超过125个汽车高科技公司在CES现场展示了最新的汽车技术和服务,而“车震”继续在MWC上演。
与CES稍有不同的是,MWC更强化了4G的色彩,因此传统手机厂商的戏份更重,三星、 索尼 、华为、联想、LG等都发布了最新的4G手机,可以想见2014年4G手机会迅速占据主流渠道,新一波换机潮也会接踵而至。
国内三大运营商的终端销售决心有可能缩短4G的普及时间窗。2014年,中国移动计划销售超过1亿部TD-LTE终端,终端补贴也可能前所未有地达到500亿元。同样,2014年 中国电信 天翼终端产业链的发展目标是全年实现天翼终端销量1亿部,其中4G终端3600万部。
新流量生意
肇始于3G时代的流量套餐,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交换单位,把语音和短信赶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流量越来越像一门生意,一头联接货币,另一头联接海量内容。
虽然抢占流量入口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但在后3G时代,在云管端的技术商业形态里,入口的概念显得更为具体和直接。有野心的玩家都在做着流量入口的梦,他们有的从云切入,有的从端切入,但眼下又多了一个从管道切入的机会——虚拟运营。
工信部在发放4G牌照的时间点几乎同步发放了虚拟运营商牌照,两批牌照共计19张,或许还会有第三批,但已经不再重要,用一位虚拟运营商高管的话说,“玩家已经足够多,接下来就看怎么玩了”。
所有的虚拟运营商被分成了四种类型:一类是特定行业、细分市场,如公交传媒运营商巴士在线、游戏公司蜗牛科技;第二类是商业零售类,如苏宁、国美、乐语;第三类是手机代理类,如迪信通、爱施德;第四类是互联网类,如京东、阿里巴巴。
外界对于虚拟运营商的一大质疑是,从国外经验看,绝大多数虚拟运营商的市场份额都不超过10%,市场空间有限。但质疑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国外虚拟运营起步于2G语音时代,虚拟运营商赚取批发和零售的差价,手法简单。而移动互联时代的虚拟运营,则势必在商业模式上有更多的排列组合。
如果不是乐语通讯集团执行总裁赵健提醒,恐怕没有人还记得11年前那个曾在新疆通信市场风靡一时的小灵通品牌“精灵通”—一个产品和套餐都重新设计过的小灵通业务,由新疆宏景通讯集团代理,赵健彼时在宏景操盘了该项目。翻开2003年媒体对“精灵通”的报道,文章中已经出现了“虚拟运营”这样的字眼,尽管官方从未承认。
这十几年,赵健走遍了欧洲、东南亚各国及港台地区,一边考察虚拟运营商在当地的发展经验,一边也在等待着中国电信业的体制松动。对赵健而言,今天乐语申请虚拟运营商的牌照也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当年他在新西兰读MBA时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虚拟运营。而赵健可能不知道的是,早在1999年,有关虚拟运营的电信改革方案已经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
香山无共识
据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回忆,早在1999年,原信息产业部在香山召开了第一次虚拟运营大会。“虚拟运营的实质是网络和业务分离(简称网业分离)。”阚凯力介绍,1998年业界就开始探讨以网业分离为切入点进行电信体制改革,香山会议正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但遗憾的是,香山会议并未达成任何实质性成果。而接下来的电信改革,无论是2001年的“南北拆分”还是2008年的“六合三”,也在诸多意志和力量的裹挟下,离网业分离的初衷越来越远。
网业分离的原理出自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罗纳德·哈利·科斯的科斯定律:在改革中,要取消各种不必要的管制,扩大经济行为主体的交易和选择空间,减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阚凯力解释,电信业的现状一是网络容量严重过剩,二是无法满足千变万化的信息服务需求。解决这一对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网络和业务分离——基础电信运营商负责管道建设和维护,业务交由其他市场主体经营。
“虚拟运营商绝不是‘代销店’,而是‘加工厂’。”阚凯力强调,虚拟运营商是以电信网络为手段提供服务,广义而言,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虚拟运营商。
其实不光是互联网公司,在还未有今天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时候,像赵健曾经服务过的新疆宏景、马化腾创办 腾讯 之前服务过的深圳润迅等等都以各种方式与基础电信运营商直接合作从事电信业务转售,虽然彼时没有虚拟运营商的身份。
身份,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商业价值,但起码在中国,身份代表了合法地位,各种游戏规则由灰变明。
上一页1 2 下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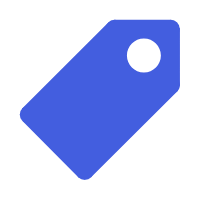 相关专题:
相关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