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卢萨卡时间,晚上八点。
在这个时间我都会准时醒来,拿起枕边的手机,查看邮箱,然后发WhatsApp消息给安竹。
一般只有在这个时间,安竹才会结束一天的工作:铺货,收款,贴广告,然后回到家里,家里才会有比较好的网络。
“周报为什么还不给我?”
“Sorry.”
“小的事情不要拖。”
“好的……”
“跟这个没关系,但是我讲一下。”安竹接着打过来消息给我,“前天晚上,我三个朋友晚上开车回去,被抢了。”
我心里一震,幸亏不是安竹。
“美国女孩子还被劫走了,让两个黑人强奸了,丢在路边,非常惨。”
“哦,Sorry,你能帮他们就尽量帮他们,工作的事不急。”
“的确太他妈的惨。”安竹是几乎不说脏话的,可见他很愤怒,“那天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我说我不去,要留在家里,差那么一点点我就会跟他们一起。”
……
安竹是我们赞比亚分公司的经理,掌管在该国的生意,三年前,他在上海的一个电商公司做市场;再两年前,他在台湾大学学习中文;再推两年,他刚刚从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Swarthmore毕业,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安竹生在美国,除小学在比利时读书外,大多数时间都在美国生活和受教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1
这是安竹在赞比亚的第二个年头。
赞比亚属于中南部非洲,这里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雨季的雨,气势磅礴,似乎要弥漫这片黄褐色土地上的一切,四个月的时间要下够一年的雨量。现在,赞比亚正经历漫长干燥的旱季,要见到雨季的第一滴雨水还要再等上四个月。
去年的雨季,赞比亚没有下够一年的雨水,处于饥渴之中,前些天朋友在Facebook上分享了她去维多利亚瀑布的照片,在照片中,世界第一大瀑布显得毫无生气。
赞比西河对赞比亚来说是重要的,它不仅造就了维多利亚瀑布的雄伟,也提供了首都卢萨卡的饮用水和整个国家的几乎全部电力。现在河水水位下降非常多,政府首先要保证饮水的供应,卢萨卡开始限电,几个月来,城市里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停电。
按照以前,我们会每天通过WhatsApp进行交流,可是最近隔几天我才能收到他的消息,因为手机也不能正常充电。
今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大幅下调,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幅度。在这之后的两个星期内,东南亚和非洲很多国家的货币也纷纷贬值,赞比亚的货币在四天之内贬值20%。我们进入赞比亚市场刚刚一年,这迎头一棒,极大考验着每一个人的耐心。
“上个月的销售,为什么还有45%欠在外面?”终于有一天,我又找到安竹在线的机会,在WhatsApp上质问他。
“这我知道,我保证,100%要回来。”
“你保证有什么用,我们会被拖死的。”
“我每天都在要账……”
“这九十万你要回来时,也就只值七十万了。”
“这我也没有办法,我跟这里的很多老板聊过,他们都经历过前几年赞比亚克瓦查的贬值,那时候,老货币换成新货币,直接减3个零,比这个还要可怕。”
“我们如果跟他们一样,那我们的生意不要做了。”我听不进去安竹的任何解释了。
对话显然是无效的。

我和安竹(最右)以及我们在赞比亚的团队 (图/刘文)
安竹和他的子公司,正面临着在赞比亚的第一场考验,也许还是持久战。而眼下还有一个考验——如何度过没有电的漫漫长夜。
安竹喜欢去酒吧喝啤酒,因为那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他喜欢认识不同的人,啤酒是他社交的方式。
可是现在看来,夜晚外出是非常不安全的。对于在赞比亚的外国人尤其如此。
现在,安竹可以把酒买回来,在家里喝,请朋友一起喝,他打开音响,乐曲缓缓流出,那是来自牙买加的雷鬼乐鼻祖鲍勃"马利的《Buffalo Soldier》(水牛战士):
Buffalo Soldier, Dreadlock Rasta 水牛战士,扎着脏辫子
There was a Buffalo Soldier 有一个水牛战士
In the heart of America 他在美洲中部
Stolen from Africa, brought to America 他是非洲偷来的奴隶
Fighting on arrival, fighting for survival 他一来就打仗,他为了活下来去打仗
……
水牛战士是欧洲人从非洲贩卖来的黑人奴隶,在美洲,他们参加了很多战争,他们去打印第安人,他们参加了独立战争,他们又打了南北战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打仗。
水牛战士从非洲去了美洲。
安竹从美洲去了非洲。
Mosi是当地的一种啤酒,它的意思是会说话的水,酿造的原料除了麦芽外还有当地的主要农作物玉米,这啤酒的烈度比一般的啤酒要强上一倍,安竹喝完一瓶,再从冰箱拿出一瓶,他一边喝酒一边跟朋友聊天,喝到嗨的时候,他会嫌音乐的声音太小,他打开车上的音响,让重低音刺激酒精麻醉的神经。
2
安竹在上海时,我跟他在一家知名电商公司里作同事。他入职大约半年多,我们都喜欢跟这个中文讲得很流利的美国人一起玩。
一次,安竹问道:“刘文,你说为什么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创新,但是我们却没有创新?上次我跟老板开会,他们讲我们网站的页面设计,一点创新也没有,那么干脆直接抄淘宝的算了。”
“这个很正常呀,既然我们做不好,那就照抄最好的。”
“可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就有创新这一条。”
“你太把这个当真了。”
“既然这么说,就要这么做。我们的企业文化不是老板制订的吗,他们为什么要做跟他们自己说的相反的事情?”
我摇了摇头,在中国,电商的发展这么快,老板哪里会有时间去想所有的行为是否跟企业文化一致呢?恐怕也只有较真的安竹,会质疑这一点。
安竹是做品牌的,市场部给他一个工作,负责所有IT开发项目跟技术部的沟通。安竹每天做得很认真,后来他发现这个工作很可笑,表面上,他需要给所有的项目打分,然后评定一个开发的优先级,实际上,他制定的优先级一次也没有真正生效,技术部的同事知道那只是个形式,真正的优先级是老板,老板要做的,一定是最优先的。
安竹在这家中国公司并不能得到重要的施展机会,他不太在意,每天还是很开心,因为有着太多有趣的事情。
他会经常跟我们去一家“地沟油”饭馆吃午饭,脏兮兮的饭馆,他也不在乎,反而觉得饭菜很可口,就把这里介绍给他的主管,那个美国人来了一次,再也没来过。
一次,我跟安竹去了汾阳路一家有点LOW的酒吧,内急的时候,洗手间人太多,我说,我们出去吧。
我们像狗一样,分别在路边找了一棵法桐,一个四五十岁的乞丐走过来,伸手向我要钱,我指了指安竹:你去问他要,他是外国人,他才有钱。
乞丐看了看安竹,说,哦,他呀,他是我朋友。
安竹提着裤子,慢悠悠地走过来,他跟乞丐打着招呼:“嗨,老梁。”
原来,这个老梁真是安竹的朋友,第一次老梁跟安竹要钱的时候,安竹说如果你真的饿,我可以请你吃饭,于是,他在路边请老梁吃了一碗炒面。第二次,安竹又请老梁去他家,这是乌鲁木齐中路的一栋老房子的车库,他们叫了一个肯德基的全家桶。后来,安竹了解了老梁作为职业乞丐的“商业路径”:老梁是安徽人,农忙时在家干农活,农闲时跟老乡一起来上海乞讨。
在这个电商公司待了近一年,一天,安竹告诉我们,他要离职了。那天安竹非常开心,像是卸下一个无意义的负担,我们都说他可以凭借好的汉语和对中国的了解,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听到别人的赞扬,他当众背诵起了古文:“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原来是《曹刿论战》。我们纷纷惊叹,惊叹之余,我也会觉得,安竹把太多的时间去学这些,太浪费时间了。
凌晨两点,我们走在徐家汇的街头,路灯非常亮,照着空旷的街道,行人很少,公园的一个角落,坐了两个宿醉的黑人,安竹走过去,跟他们抽烟聊天,我们只在远处看着。他回来跟我们讲,他知道上海的很多黑人,圈子很小,生活这个城市的边缘,甚至于依靠卖毒品生存,不过,他们只卖给白人,因为怕中国人会告密。
3
再次跟安竹联系,已经是一年之后了。电话里面他说自己又离职了,想问一下我的情况。
我同两个合作伙伴刚刚创立了一家公司,在非洲销售手机。三个月前,公司在非洲的马拉维派驻了第一个员工。现在,公司雄心勃勃,想去马拉维稳固一下公司的发展,然后在赞比亚拓展业务。
我对赞比亚并不了解,更没有合适的人选去掌管这里的业务。于是,我对安竹说,加入我们吧。
我们又多买了一张安竹的机票,踏上了非洲之路。

马拉维是赞比亚的邻国,人均GDP一年只有200多美金,现在刚刚结束总统选举,一个新的总统上台。
这是安竹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新鲜的冲击让人兴奋。他告诉我一个现象:马拉维很多当地人穿的T恤都是美国某所高中的学生校服,或者是某个组织的文化衫,有一次他竟然发现了他读过的高中的文化衫。于是,每天走在街道上,他都会偷偷拿出相机拍照,拍各种不同的文化衫。
后来,我也去拍非洲人穿的T恤,当你看到非洲人的衣服上面,有的写着“富士康”,有的写着“平安财险”时,真是非常有趣。之前,他们穿欧美的二手衣服,现在,穿中国来的二手衣服。
安竹一直保持拍照的习惯,他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在马拉维的首都利隆圭,一些国外的商人建了酒厂,制造一些非常廉价的酒精饮料,供应当地市场。为了扩大销量,他们把酒精饮料做成小包装,这真是一个灾难,因为很多孩子会去买这些廉价饮料,也导致了对酒精上瘾,一些饮料含有工业酒精,发生了多起中毒致死事件。政府虽然想制止酒厂生产小包装的饮料,但在这样的国家,法规的执行异常艰难。
安竹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后,他就去拍人们扔在地上的酒精饮料包装,相机里存有形形色色的包装照片,其中也有中国的厂商生产的,当安竹给我看照片的时候,我会有隐隐的不快。
在马拉维,也有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我们会带安竹去跟不同的中国人聚会。人们很少见到中文这么好的美国人,在餐桌上,中国人有时会对安竹讨伐美国,有时会让安竹背诵一段中文文章,他开始背诵朱自清的散文《匆匆》,第一次,他甚至能够背诵全文,后来就越来越少,有一次,在我们都等着惊叹的时候,他只背了第一段。后来,安竹就没有再进行过这种表演。
安竹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利隆圭的citycenter是当地的一个购物中心,我们会坐在那里喝啤酒,听当地艺人弹着木吉它唱歌,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艺人,二十多岁,患有白化病,人们已经完全看不出他的肤色。安竹了解到白化病人在当地的状况:这些人一般很难找到工作,不仅如此,当地人认为白化病人的器官有某种神奇的作用,因此,有的白化病人会被劫持,割掉胳膊或者腿,有的死后还会被掘走尸体。
安竹对这类问题刨根问底,有时我会把它看成发达国家国民的高傲,站在一个高高的平台上去俯视落后国家。
4
到赞比亚的第一天,我们在一户当地人家吃晚餐。主妇的儿子在上海读书,是安竹的朋友,做客那天,她想借机把侄女介绍给安竹。就餐时主妇问了我一个问题:是否中国人喜欢吃狗肉?原来,几个月前有一些中国工人请当地人给死狗剥皮,大吃狗肉,此事上了当地的新闻。
赞比亚虽然落后和贫穷,却并不单一。
Great East是卢萨卡的主干道,这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时期修的水泥马路,路边移动运营商推广4G移动网的广告则让你觉得这里发展很快。路边有印度人修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出入着本地的有钱人,他们大多是公务员;这里的白人大多是一些联合国和NGO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欧洲游客;也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一些商业机会的掘金者,或是中国企业的员工。
我们公司的发展开始并不容易,为了注册公司,一次次地跑政府机关,一次次被可笑的理由敷衍,效率低下。一天,在当地最大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就登了一则中国人行贿当地官员的新闻,标题是“中国承建商是行贿专家”。中国人在赞比亚承建很多工程,修路,建体育馆,建开发区,有利于当地发展,不幸的是,一些承建商为了得到工程项目的承包权,去行贿当地的官员,甚至中国形象因此受损。

赞比亚的团队一起聚餐 (图/刘文)
那天去超市买食物,路上我们车开快了一些,一个北非人在车里拿出这张报纸摇着,表示对我们的抗议。后来几天,我们都不好意思出门。
各种压力下,也许我太过敏感,会被一些小的事情伤害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
一次在路边,安竹买了一个老女人的食物当早餐,我跟他讲你不要吃,这个太脏了,他回答我说,这总比中国的食品更安全一些吧。
在工作上也发生了冲突。公司需要在当地招聘一个司机,在报纸上发布了招聘启事后,前来面试的络绎不绝,我们只要一个司机,可一天来面试的有几十个,很多人都是带着亲手写的简历和求职信,换上他们最好的西装,辗转乘坐几次巴士,来我们办公室递交简历,拒绝他们非常困难,安竹一个接一个地面试,可谓精挑细选。
没有想到,安竹把一个有7个孩子、年纪58岁的老人作为首选,这让我大为光火,即使再动恻隐之心,我也无法接受一个如此年龄的老人在一个创业的公司,安竹列举了他的种种优点,例如,他不仅有很长的驾驶经验,还懂得修车,也懂得急救,他在津巴布韦的军队工作过六年。我想安竹列举的理由也许并不是他真正内心所想,这个老人总共养过14个孩子,现在还有7个孩子,亲戚养不活的孩子的都送给他了,安竹虽然职业,但是他的善良会在潜意识中左右他的决定。不管安竹如何坚持,我最后还是拒绝了。
还有一次,会计闲聊时问安竹为什么来非洲做生意,安竹讲,他是为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会计又问他,你的合作伙伴为什么来这里?安竹讲,这个我也不知道,也许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过更好的生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这个回答触动了我的神经,我质问安竹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明明说过,是想在非洲做一家能够带来改变的公司,不只是为了赚钱,不是养家糊口,如果仅为了家庭,我们完全不要到这种地方来。
我们一次一次地冲突,身心疲惫,不过在非洲的好处是,你在这里没有其它可以依靠的人,只能一次次的和好。某个深夜,我们照例喝着Mosi,望着非洲深邃的星空。安竹说:我们如果是同事,就不能是朋友,刘文,你总不明白这一点,看来我们难以合作很长时间,我帮你三个月吧。
那时,我觉得我不能失去安竹,我说:三个月不够,我要一年。
安竹想了想,他说:好,我做一年。
我要回到中国了,走之前,我细致地罗列了所有对安竹的要求,例如,恪守每天的日报,个人喝酒的消费公司不做报销,非休息日不能饮酒等,我写了很多,我想好好跟安竹谈一谈,但到了最后,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发现我能选择的就是两个字:宽容。
我回到了上海,安竹留在赞比亚,他自己一个人。
5
我和安竹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同事关系,每天的交流是日报、周报、开拓市场、招聘当地员工,我知道只要我们制定每一项任务的时间结点,做得就不会差,因为安竹是一个诚实的人,这种诚实是非常多的中国人所欠缺的。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几个月内,安竹就拿下了当地最大的连锁零售商,我们的产品与一线的手机品牌三星、华为等摆在了一起,再后来,我们销量超过了三星,接着超过了华为。安竹把一个来自深圳的山寨品牌做成了当地的名牌。
到了圣诞,也许是太忙了,也许是忽略,我忘记了这个西方习俗中最重要的节日,安竹一个人在非洲,度过了一个孤独的圣诞。我至今保留着他在圣诞夜发给我的一段话,他说:刘文,我在这里非常孤独,我一个人,在电脑前,在看一部电影……从他有点沙哑迟钝的声音中,我知道,他一定是喝了很多酒,又抽了很多烟。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有些自责。

我经常翻看办公桌上摆着的长长的一排书,那是安竹决定去非洲后留在这里的,他说他非常爱上海,甚至把上海当成了他的家,但是要离开了,这些书他不舍得扔,就放在我这里,大部分是厚厚的中文书,有梁思成的建筑书籍,有台湾的小说,还有科幻小说《三体》,大部分非常新,也许,安竹是想以后再去读。安竹会不会忌恨我呢,去了非洲,他失去了上海的人脉,中文也有可能变得生疏。他在台湾和大陆,有五年多的积累,现在失去很多。
为什么如此喜欢中文,安竹跟我讲过他读懂的第一首唐诗,“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唐诗的美,在他的心底产生强烈的同理心,这种感受让他永远保留对跨文化的兴趣。
在卢萨卡北面,有一个小山包,名字是Leopard’s Hill, 看到这个名字,我说可以翻译成豹子山,安竹说应该叫豹丘,因为丘比山小。我非常喜欢这个翻译,丘这个字,在现在的中文中很少使用了,安竹这个翻译显得很有诗意。也许是因为他在台湾待了三年的原因。
尽管在一所优秀的学校读了经济学,进入了华尔街,可是他不喜欢,他去了台湾,学习中文。
父母希望他回去再读一个法律学的硕士,成为一个律师,安竹没有回去。他来到了上海。上海是放大版的台北,并且,放大的不太一样了,安竹这样说。
安竹讲过他想去一所美国的大学,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可是,他发现每年申请这个职位的有一百多人,可能最终只取两个人。他觉得他的积累不够,就一直没有开始。
6
我又回到非洲去看我们的生意。
过海关的时候,即使有签证,海关人员还是刁难我,不让入境,理由是很多做生意的中国人在这里非法滞留。安竹帮忙找了一个当地人,据说这个人的哥哥相当于该国公安部长,一通电话后,我过关了。
第一天我们到酒吧喝酒到很晚,第二天早上,看上去睡意朦胧的安竹扒几口女佣做的早餐,带上一杯咖啡,坐上车子,简单问候Good Morning后,司机就开动了车子,他养的一条罗威纳欢快地追着车子跑,安竹跟它打着招呼,车缓缓驶到院子门口,开院门前,园丁熟练地把狗按倒,避免它危险地跑到马路上。安竹很爱他的狗,他也教会其他人如何关照他的狗。
在车上喝着咖啡,安竹会看一份南非报纸,他嫌当地的报纸“大多没有深度”。到了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公司的规章制度,组织架构,月度目标。维修人员专注地修手机,销售总监打开报表,打电话联系要拜访的客户,各项事务井井有条。我经常对安竹说,什么时候做到公司没有我们也可以运转,那就是成功了。

我们在马拉维的团队 (图/刘文)
下午去一个当地中餐馆,全体员工为一位同事庆祝生日。我们刚刚招聘了几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开心是他们对工作的最初诉求。就餐时安竹进行了一个游戏,他在网上找了很多字谜,让这些年轻人来猜,每猜对一次会有五元钱的奖励,年轻的同事乐此不疲。餐后他询问每个年轻人是否已经办了银行卡,原来他要求大家每个月能够拿出部分工资存起来,两年之后可以开始大学的学业。
吃完生日餐,我们又聊了一小时工作。晚上七点,夜色中的酒吧开始有了韵味,环顾四周,人越聚越多,暖暖的灯光很黯淡,服务员端着啤酒穿梭,这气氛让人忘记了是在非洲,安竹的眼睛里面也开始泛光,我们叫了啤酒,边喝边聊,安竹开始打量四周有没有他感兴趣的人,在酒吧中,分辨出一个当地人,或者是一个外地人,一个土豪还是一个白领,是安竹的爱好。
那天晚上,我们认识了一个在坦桑尼亚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头,讨论了在那边合作手机生意的可能性。为示友好,老人请我们干了一杯据说能够壮阳的当地药酒。
后来,安竹又发现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印度人,他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的MBA,有非常好的背景,现在为一家国际知名药企在非洲拓展市场。在这里找到一个受同等教育的人并不容易,安竹跟他聊了很久,后来,我们又在印度人住的酒店喝了很多。我撑不住了,要回家睡觉,安竹说,他还要去见一个开酒吧的朋友,今晚约好了谈一点事。
凌晨三点钟,我睡得懵懵懂懂,安竹回来了,他敲我卧室的门,让我出来一下。
安竹呼吸的酒气很大,后面是一个胖胖的当地黑人,再后面又跟了两个黑珍珠般的漂亮女人。安竹指着我,用英语跟黑人说:“这是我的老板,他是中国人。”他又用汉语跟我说:“这个人就是今晚我约见的,他在这里有好多酒吧,他想投资我们的手机生意。”
我想着如何跟这个当地人寒喧,安竹却说:“你可以去睡觉了。抱歉打扰你,我只是让他知道,我背后有中国人,你知道的嘛,在非洲,中国人就代表着有实力,有钱。”
安竹大声放着音乐,继续喝酒,他毫无倦意,后来,两个黑珍珠再也熬不下去,就离开了,她们本来想着今晚也许会有生意,再后来,那个当地人也离开了。天都快亮了。
“刘文,你以为我的手机是怎么卖的,都是在酒吧里卖的……”安竹嘟囔着,天亮了,他要去睡觉了,今天是周末,他会睡到下午。
网易“人间”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 thelivings@163.com,否则将被追责
作者:刘文 | 破茧计划应用数学学士,计算数学硕士,喜欢科幻,目前创业,在非洲多个国家拓展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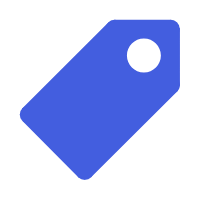 相关专题:
相关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