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记者 丽案调查工作室 丁雪 侯懿芸 吴海浪)在经历智能手机对友情、亲情的稀释和对自己逻辑和创作的影响后,他们决定逃离:使用非智能手机。他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联盟:反智能手机联盟。
在周围人的手机屏幕越来越大时,他们的却越来越小;在一群彩色手机中间,他们的黑白手机尤为扎眼;在地铁上一群低头刷屏的人中间,他们手中的书显得分外的沉。
他们也因此和周围人格格不入,手中的非智能机被当成遥控器,也多次被领导暗示换一个手机。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也收获了真正重要的情感和受自己控制的时间。
尽管在时代的大潮下,他们也不得不因为工作等原因选择和智能手机某种方式的妥协与和解。然而他们仍和它保持距离,想留一段不被“控制”的时光。
“反”的理由工作和聚会时间都被切成碎片
“在参加项目的那三个月时间,我很少上网,手机几乎没开,不需要看邮件,不需要刷微博、微信,不需要使用手机。只需要跟周围的朋友联系,只需要关注眼前的事,和身边的风景,会感觉到返璞归真,也开始清楚那些对我们真正重要的情感和观念。”
他叫魏明,豆瓣小组“反智能手机联盟”创始人。“没有智能手机照样走天下,不用天天充电,只发短信打电话,我的生活也很好!”在豆瓣里打开“反智能手机联盟”的小组,页面上赫然挂着上面的几行字。
谈到自己2010年时参加的那个去美国小镇的项目,这个26岁的陕西男生仍印象深刻。“回来后我一直很自豪地告诉我的朋友,两个半月自己都没碰过手机,甚至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用。”
魏明告诉法制晚报记者,“上大学的时候,自己用过一部索爱的智能手机。用完之后就觉得没多大用处。”
“当时特别讨厌智能手机的一点就是需要每天一充,感觉把人像狗拴在家里一样。”魏明补充道。
此外,魏明讨厌这种时时在线的感觉,以及由此带来的时间的碎片化。
“我之前感觉智能手机可以让你充分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但其实用多了,就会觉得反而是智能手机把你的时间碎片化了。”
他举例子说,比如大家在一起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工作的时候,那些即时软件一直在响的话,你的注意力就会分散得很厉害,慢慢地,你整个时间就会变得碎片化。
魏明一直对朋友出去玩大家都在看手机这个事儿很无奈。“如果那样,还出来玩什么,干脆大家都回去玩手机好了。”
他讲到,有一次聚会,“我们就开玩笑,说大家把手机都拿出来,谁第一个看手机谁就请客。”
“有一个女生喜欢刷微博,她就真的去看手机了。”魏明说。
劝妈妈跳广场舞别窝家玩手机
30岁的上海女孩范小弱对于魏明提到的这些感同身受。她也是115个“反智能手机联盟”成员中的一个。范小弱坦言,她经常会因为自己老公总爱低头看手机而吵架。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低头玩手机。”这个网络上流传的抱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范小弱和她老公的真实生活写照。
“我们以前在一起,他就老是看手机。有时候我们一起坐地铁或者公交车的时候,他一上车就不自觉地把手机掏出来看。我希望我们一起出来就坐在一起聊聊天。而且我跟他讲话,他也心不在焉。”
范小弱已数不清因为手机的问题和她老公吵了多少次。
更让她害怕的是,自己的妈妈也在天天玩手机。
“我经常劝她出去运动一下,哪怕是去跳广场舞,不要老窝在家里玩手机。”范小弱总是苦口婆心地劝,但收效甚微。
后来,范小弱甚至想给沉迷于手机的妈妈换一个非智能机,但这个想法很快被妈妈拒绝了。
妈妈和妈妈的朋友依旧在朋友圈转发带有“太恐怖了”“看的人都转了”“不转不是中国人”字眼的谣言和鸡汤,乐此不疲。
妈妈也喜欢吃饭的时候拍照。“我就觉得手机的毒害太大了,把我妈给害了。”范小弱叹了口气。
早上刷个微信20分钟就过去了
“手机让我们变得粗鄙,通过手机语言,我们在‘粗鄙的享受’,内心很难滋生并回味出‘很讲究的情绪’。”
自称“不用手机”的作家毕飞宇在《写满字的空间》中说的这些对于杨友三来说很受用。
“以前写书能写四到五个小时,但是用智能手机以后就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早上起来刷个微信,20分钟就过去了。那时候我一天到晚都处在这个状态。”深知智能手机是阅读和写作大敌的杨友三一直对它敬而远之。在上海做自由科学作家的他坚持用诺基亚功能机。
杨友三还能举出许多其他创作者的故事,“《三体》作者刘慈欣曾说,他不使用微博和微信。只要关闭电话和邮件,就可以专注于写作。另外,网上也有传《盗梦空间》的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不使用电子邮件。”
基于此,杨友三在今年加入了反智能手机联盟。
真正让“反智能手机联盟”成员们恐惧的,是智能手机对自己潜移默化的改变。
胡晨也在今年和杨友三差不多同时加入了反智能手机联盟。
“我2007年用的智能手机,大概用了1年,就不再用了。因为我觉得它会阻碍思维的严谨。包括我的表述方式也会受这个影响,变得碎片化而没有逻辑。”
眼前这个高高瘦瘦身穿白衬衫蓝色牛仔裤的北京男生胡晨,今年27岁。他说自己有写作的习惯,但发现用了一段智能手机以后,很难把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结合在一起,“写一段这个,想到那个又写那个,我就会觉得变得更意识流。就跟微博一样,每条信息都是短的碎片化的信息。”
“智能手机的方式是一种反阅读性的。包括我再回到书籍深阅读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很难深入。”这种变化让胡晨害怕。
此外,胡晨说,本来应该被留白的时间,也渐渐被智能手机所填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无意义的填充。
胡晨举例,在地铁里面或者空余的时间,你都会想要看手机,会对这些上瘾。比如你想看体育新闻,结果看到了别的推送新闻你就再看看那个,到最后你甚至会忘了最开始想要干什么。
“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被控制的,会无意识地接收很多无用的信息。”
智能手机这种无孔不入的“控制”,让胡晨决定逃离。
他开始使用非智能机。
他开始通过电话和直接见面的方式和朋友联络感情。胡晨说,在不用智能手机的那段日子里,自己有事就通过电话或者邮件和大家沟通。
他开始通过问人和别人沟通这种质朴的方式去找路。胡晨说,他享受这种和别人交流的过程,他觉得,智能手机很大程度地代替了与人沟通的乐趣。
“当然也会出现别人指错了路,我们走错了的时候。但我觉得这也是有意思的一部分。”胡晨对法制晚报记者说,“其实你的时间没有你想象中的宝贵。”
“反”的尴尬用非智能手机却被当成遥控器
同样是反智能手机联盟成员的范小弱也有类似的生活模式,她说,在工作回家坐地铁或者在路上的时候,自己一般会随身带一本书。“我专门买了一个双肩包背着这些。如果我用智能手机,在地铁上像其他人一样刷机就把这些时间都浪费掉了。”她说。
2004年开始用手机的范小弱仍清楚地记得自己用的第一个手机是西门子的蝎子手机。“后来陆续用过松下什么的,但还是诺基亚的手机居多。我不用手机上网。”
当然,自己一寸多的屏幕也会在一群四寸、五寸甚至六寸的手机屏幕中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范小弱在医药企业做内勤。“之前有一次开会,我的手机就放在桌上,有一个经理看见了,他就说‘哎?这是什么,一个遥控器啊?’他说你开会拿个遥控器过来干吗啊?”
范小弱被弄得哭笑不得,不得不解释说:“这是我的手机。”
经理听了之后很诧异,皱了皱眉头说:“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手机?”他觉得很奇怪。
与此同时,范小弱表示,自己也被领导多次暗示,“你什么时候去换个智能手机啊?”
“领导感觉联系我不是很方便,因为我有时候会听不到电话铃,因而接不到电话。他们有时候在工作群里面讨论问题,我也参加不了工作的讨论。”范小弱说。
后来,领导就干脆直接问她,什么时候会换一个智能机。
“我就说自己不太喜欢用智能手机。”范小弱说。
参加活动没微信只能单独通知
同样用非智能机的胡晨也会经常受到老板的提醒,老板对胡晨半开玩笑地说,“换个智能手机吧”。
“我比手机聪明,不用智能手机。”胡晨也经常半开玩笑似的回应。
“部门要组织活动,大家在微信群里沟通,大家会单独来通知我。”胡晨也颇感无奈。
很多人干脆会直接因为花费原因减少和胡晨的联系。毕竟给用非智能机的胡晨打电话比给他发微信、qq要贵很多。
胡晨自己却并不太介意这些。“这正是我追求的,因为很多在微信上的联系都是不必要的联系,而且要花很多时间等别人回复。我觉得这都没有打电话,或者见面吃顿饭、喝点酒这样来的效果好。”
有时抱怨也来自家人。
一次,胡晨开车带着家人出去玩。由于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导航,胡晨只能买地图、看路标。反反复复开错了好几次后,还要再返回去找路。家人很不高兴,抱怨胡晨说这样太费事又耽误时间。但他认为,这也是一种经历。
反智能手机小组线下活动不多
男:“我和几个朋友上个月成立了一个‘反智能手机’组织,目的是呼吁大众摆脱智能手机的控制和防止对智能手机的上瘾。你愿意加入我们吗?”
女:“听起来真棒,那么我该怎么做才能加入你们?”
男:“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和豆瓣小组……”
类似的悖论被编成段子在网上流传,却也是魏明、范小弱、杨友三、胡晨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事实。
反智能手机联盟是魏明2012年在豆瓣上创建的一个小组。魏明说,“平时大家主要是在线上的豆瓣小组里发帖,线下活动并不多。”
胡晨也说:“我们这个小组是比较分散的,大家都在全国各地,主要是有共同的反思和习惯的一个聚集,不一定要以见面的形式去实现。”
“反”的结果大多数人已投降但能约法三章
在魏明、范小弱、杨友三、胡晨这些80后当中,只有范小弱在一直使用自己的非智能机。“但我还会使用iPad,只是在路上我一般都不会用。”范小弱说。用反智能手机联盟中的另一个组员蔷薇的话说,“群里大多数人都已经投降了。”
经历了一番挣扎后,杨友三不得不又买了一部安卓的手机。
客户让杨友三帮忙维护微信公众号。为了生计,他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但他给自己约法三章。
“假如有任何软件发通知给我,如果不是特别有必要,我都会在设置中禁止这个软件的通知功能。由于微信用得最多,提醒也最多,所以需要关闭的功能也最多。我关闭了朋友圈,同时将所有的群都取消了新消息提醒。”
“即便如此,我还是会主动打开微信,去看微信队列中不断涌现的聊天内容。”杨友三无奈地说,“我已经彻底被智能手机搞烦了。”
“智能手机给我呈现了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将我牢牢套住,彻底消灭了我的专注力和创造力。”
杨友三终于决定,把智能手机关了,开始重新用诺基亚。为此,他在反智能手机联盟小组里发了一封长长的帖子,像是一种仪式性的告别。
如今在做人力资源方面顾问工作的胡晨也在今年6月份买了智能手机。他说因为工作需要用到微信。“联系的人太多了,每天都发短信的话成本会比较高。”
但胡晨有自己的平衡之道。
其实人可以有意识控制,每天几个小时,可以尽量去不用或者少用手机,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胡晨告诉法制晚报记者,“可以让这些慢慢成为一种习惯。”
“因为你很难想象再过十年二十年,手机变得更智能。然后就会像科幻片里演的那样,人出去以后,会有一个轮子驱动你前进,椅子上方有一个手机,你想去哪轮子就带你去哪,你一边走一边看着手机,人完全被机器控制。那样太可怕了。”胡晨说。
从最开始激进的反对到倡导少使用到后来的反思,魏明承认,自己对智能手机的想法从开始是有变化的。这背后是手机从键盘到触屏,从单核到多核,从单纯的电话短信功能到后来的上网、办公、理财、支付……手机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存在之一。
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在这个设备里,而变化纷繁复杂,甚至快到我们来不及界定自己和它的关系。
魏明说他喜欢《好奇心日报》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智能手机在现在环境里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怎么使用,完全要看自己,一定要做到线上生活和线下生活的平衡。不是说所有的科技进步,一下放在自己身上就是有好处的。
毕竟,科技本身没有错,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对自己缺乏自控力而感到沮丧。
(文中魏明、范小弱、胡晨、蔷薇均为化名)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
实习记者丁雪记者侯懿芸
摄/记者吴海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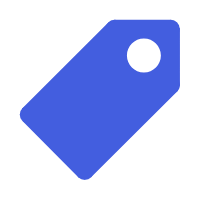 相关专题:
相关专题:




